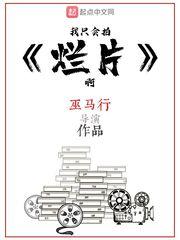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 85 章(第2页)
程西惟默了默,他的话像涓涓细流,点点滴滴地汇入她的心间。她想了想说:“景忱,其实我也一直不敢回忆,有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的我们就像两个被关在笼子里的疯子,互相撕扯、头破血流。”
寂静的夜色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两人的心房。
孟景忱叹了口气,想了想问她:“还疼吗?”
程西惟没回答,反问:“你呢,你还疼吗?”
孟景忱闭上眼睛,低声道:“我也不知道,说不上来。”
程西惟余光朝他侧脸瞥了一眼,也低低地说:“其实我现在也说不清那些伤口究竟是被我治愈了,还是被我藏到了看不见的地方。大多数时候,我的意识都在告诉我要往前走,可是前面究竟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只是觉得总归不会比留在过去差。”
孟景忱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带着点小心翼翼:“如果前面又是我呢,你怎么办?”
程西惟这时才转身看向他:“那你呢,如果你往前走,碰到的又是我,你怎么办?”
这回孟景忱没有沉默,几乎是接着她的尾音跟上一句:“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他说完,也转过身,与程西惟面对面。昏暗中,他抬手摸了摸她的头发,又低低地说:“可我很怕你把我当成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程西惟没有回他,孟景忱的心一点点沉下去。也不知过了多久,耳畔轻轻响起她低柔的声音:“那不至于。”
孟景忱心脏猛地一跳,他愣愣地看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有什么滚烫的东西顺着他的眼角往太阳穴流去。
他抬手盖住双眼,下一秒,手心便潮潮的。
程西惟静静地躺着,她能感觉到身边的男人正经历着情绪的巨大波动,正想着要不要抱抱他,却不想,身边那团热源倏地靠近,他用他有力的臂膀,将她整个圈进了怀里。
接下去四天,程西惟继续《寻筝记》的拍摄。
孟景忱白天一直呆在酒店处理公务,到了晚上程西惟收工,他便陪着她在阿拉木图随处逛逛。来哈萨克斯坦短短几天,程西惟几乎已经把阿拉木图几处景点逛了一遍。
来哈萨克斯坦的第五天正好是周末,剧组难得放一天假。正好孟景忱也不需要加班,两人约好一起去哈国首都努尔苏丹的巴伊杰列克景观塔。
程西惟早在两天前就已经买好了机票,大约九点左右在纳扎尔巴耶夫机场落地。
谁知去机场的车上,她就接到了艾草的电话。
程西惟心情不错,接通电话时,说话都拖着软软的长音:“歪,什么事?”
电话那头却传来一声压抑的啜泣,程西惟心头一揪,坐直了身体问道:“怎么了?”
“西西,羡羡自杀了。”
短短几个字就像炸|弹,轰的一声在程西惟脑中炸开,她的双眼慢慢地失去了焦距。
程西惟嘴角不可抑制地抽搐了一下,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今天不是愚人节……”
车外灿烂的阳光打在她的身上,可程西惟却觉得一阵阵发冷。
电话那头艾草还在说些什么,但她已经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只木讷地重复:“不会的,她不会的。”
艾草还在说话,程西惟骤然提高了声音:“我说了她不会的!”
孟景忱早已察觉到不对,连忙抢过了她的手机,却不想,电话那头也已经换了一个人,竟是纪修。
孟景忱一边跟纪修了解情况,一边不放心地搂住程西惟。
程西惟在最初的茫然之后,像是终于接受了何羡做傻事的事实。她缓缓地低下头,佝偻起自己的身子,试图把自己缩成一团,这样就可以抵御这个可怕的消息带给她的冲击。
孟景忱挂断电话后,直接在她手机上改签了回国的机票,随后又找到微信上的《寻筝记》导演头像,帮程西惟请好假。
做完这些后,他抱住程西惟,双唇在她发顶轻轻一吻,低声道:“
绿茵之寒冰射手
从崇明岛走出的青训教练,而立之年,碌碌无为一朝回到半生前,足球系统,降临身边从冰块小子到寒冰射手,再往上,那是高处不胜寒齐策回到了2007年,完成那未竟的足球梦想足球与生活,笑谈中淡泊...
我只会拍烂片啊
你们信吗!我说,未来我们将创造一个时代,一个让好莱坞都颤抖的时代,那个时候那一年,燕影大学混吃等死,被辅导员称为老鼠屎的大四学渣喝醉酒对着兄弟们吹了这么一个牛逼,他本来以为也就吹牛逼,酒醒后...
美食生香:农门长姐发家记
农门酒菜香,长姐赛儿郎,盖作坊搞批量,修花圃制美妆,带领全村老少向前闯,喜迎美好生活绽光芒。...
冷冰萃云(包养|伪骨科1V1H)
BG年上七岁年龄差包养伪骨科替身妹妹的失踪是他难以释怀的罪,徐谨礼怀着歉疚离家四年,无意间撞见了一张和妹妹极为相似的脸,可却在认识的第一晚和她上了床水苓总觉得男人像冬天挂在云杉枝头的雪...
安小海刘俊全文免费
三十年前,安小海被人层层设计,失手杀人,身陷囹圄。眨眼间,从人生的巅峰跌到了谷底!二十年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涯将他摧残得不成人形!出狱后艰难挣扎十年便郁郁而终。安小海穿越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身上,上天给了重生的机会,安小海不愿再次错过!为什么一个大学生会被如此针对?为什么自己会被如此残忍的对待?为什么那背后的黑手就是不愿意放过自己?安小海拼尽全力,戳破重重黑幕!为了活下去,为了有朝一日沉冤得雪,安小海周旋于各种各样的危险之间,抽丝剥茧间,一个巨大的阴影渐渐的浮现出来!这一次,安小海不再是曾经那个柔弱的羔羊了,看他如何绝境反杀,翻云覆雨!!!...